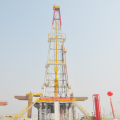能源審批權下放 謹防“4.95”現象重演
“準生證”到底由誰說了算?這個業界爭吵了許久的問題,終于在近段時間得出答案。在近期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審批權下放被多次提及并討論,與此同時,作為新一屆政府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審批權下放亦備受市場各方關注。這著實稱不上是第一次傳出此類消息,但經國務院證實的還尚屬首次。
面對新一輪的政府職能改革,市場能否迎來真正意義上的“政策福利”?在歡呼“政策春天”已近的同時,我們在這里也有必要對此進行理智的觀察與反思:審批權是否“一放了之”?
“政策福利”腳步將近
幾年間圍繞政府審批權的討論,不斷翻騰、沉沉浮浮,時至今日這一切終于塵埃落定。根據幾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的內容可以確定,減少行政審批已成為各部委當前的一項硬性任務,未來審批權逐漸分批下放已毫無懸念。
此輪改革涉及到電力、能源領域的審批權,主要包括:除在主要河流建設以外的水電站、分布式燃氣發電項目、燃煤背壓熱電項目(熱電聯產項目)、風電站項目核準、國家規劃礦區內新增年生產能力低于120萬t煤礦項目、除跨境(省、區、市)外的油氣輸送管網項目、330 kV及以下交流電網項目、列入國家規劃的非跨境(省、區、市)550 kV交流項目。此外,原來由國家能源局審批的“電力用戶向發電企業直接購電試點”、“電力市場份額核定審批”也被取消。
“對于很多投資和項目而言,審批權過于繁瑣會妨礙市場發展和企業參與的積極性。”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孟憲淦認為。
比如,一個水電項目前期工作十分漫長,除流域規劃之外的工作,前期工作少則5年,多則數十年。一般大中型以上水電項目可行性研究過程要完成40~50個專題報告,約30個報告需要有關部門審查。在國家層面的審批涉及水利部、國土資源部、環保部、電網公司、鐵路部門,最后是國家發改委及國務院。因此工程建設期的時間很大程度取決于行政部門的審批時間,一般100萬kW水電站建設期不會少于5年。
因此,很多項目因需大量的政府審批而被擱淺,坊間更經常形象地用“跑項目”來形容投資者的窘境。
“除了一些重大、敏感項目外,企業應該比政府更了解情況,他們簽訂合同時肯定會很謹慎,應該有一定的自主權。減少審批可以減少政府干預,提高市場化水平。”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何曼青說。
從支持企業發展的角度出發,各方對國家下放審批權大加贊賞。
謹防“4.95”現象重演
行政審批權減少后,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將不再面臨“先生孩子,后拿準生證”的困擾,然而人們發現,他們將不得不面對新的挑戰:如何才能保證地方政府正確行使相關權力?減少地方保護主義、“權力尋租”等詬病的出現?
人們提出這樣的質疑,并非沒有依據。事實上,在最近幾年的發展中,我國新能源產業已用慘痛的經歷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2008年金融風暴之時,中央“4萬億”投資應聲而起,緊接著實施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當時5萬kW以上風電項目由國家層面核準,5萬kW以下由省級政府核準,而在地方政府積極推動下,一些發電企業打起“擦邊球”,將大型風電項目分拆成多個小于5萬kW、多為4.95萬kW的小項目進行申報,并一舉獲得了批復。
于是一時間,造成局部地區風電接入過于集中的局面,而當時由于電網公司尚無接入大容量風電的能力,導致了已發出的風電根本無法并網,浪費了大量的市場資源。
此后,針對各地頻發的“4.95”現象,國家能源局不得不做出調整,在2011年回收了地方政府風電項目審批權,要求各省核準風電項目前須先向國家能源局上報核準計劃,這才阻止了這場“投資災難”的繼續蔓延。
事實上,權力下放地方后,引發的后續隱患屢見不鮮。
同以風電為例,新能源因前幾年較為火爆,再加之國家給予了相應的扶持,而被地方政府作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于是人們看到,在后來的發展中,地方政府或要求投資者必須使用本地生產的風機設備,或需在當地建設相關生產基地。而作為弱勢一方的投資者,為順利拿到路條不得不照此執行,這成為國內風電設備行業此后產能過剩的一大重要原因。
中電聯副秘書長歐陽昌裕認為,審批權下放后,需要高度關注中央與地方之間規劃統籌和協調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好,有可能又回到2011年以前那種混亂和無序建設的狀態。”
因此,綜合來說,審批權下放到地方政府后,如何約束地方的投資沖動和行為,是一個問題。目前正值地方政府財力不濟,加之地方政府多不如中央政府規范,有可能引起地方政府大上項目,并在過程中引起群體沖突。因此,有效規避這一問題,成為檢驗審批權下放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審批權“一放了之”?
審批權下放,從操作層來說將會較為復雜,比如:具體涉及到哪些權力?又將會下放到哪個層級?補貼由誰來發放?若導致類似風電行業的問題再次出現,責任將由誰承擔?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認為,由于地方政府的特殊利益關系和發展導向,下放審批權給地方政府,是否可以達到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是存在疑問的。審批權“收與放”的意義遠非想象中那么大。
在中國的現實大多是,政策一經宣布,各方嘩然而上,而事實上,相關配套與落地政策還尚未出臺,盲目投資亦常令投資者“撲空”。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周大地認為:“改革并不等同于放權,審批權下放不等同于隨便放手。現在包括能源在內的很多領域,在地方競相上馬、出現投資過度的情況下,一味地強調放權的做法并不合適。解決這一問題重點在于加強規劃和控制。”
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王元京建議,比如影響企業直接決策的審批權就要取消,避免過碎、過細,阻礙經濟活力。另一方面,涉及到環保、安全等方面的項目,雖然不用集中由中央來批,但是要由法律法規逐漸代替行政,用各級部門執法的方式來實現。此外,該批的事項還應逐步公示,促進審批的透明化、標準化、公開性。
與上述兩位“審批權部分下放”的觀點不同,林伯強則提出可完全取消行政審批權,建立審核準入制,在此基礎上,通過提高準入的門檻,抑制產能過剩。在他看來,在行政審批下,有渠道資源的企業往往具有優勢。而在審核準入制下,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競爭優勢的企業將具有優勢,符合市場的優勝劣汰原則,同時又可避免行政審批下滋生的尋租現象。不過他同時強調,對于新能源產業而言,由于前期發展投入較大,還需要加大政策扶持與財政補貼,同時建立公正平等的市場準入制度,以此來保障新能源產業健康發展。
因此,就目前來說,審批權下放還須包括價格改革、利率市場化、行政效率提升、法制更加完善在內的一系列改革。同時要加強監管,建立起一系列配套的約束機制。說到底,無論出發點多么完美的政策,人們看到的終究是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