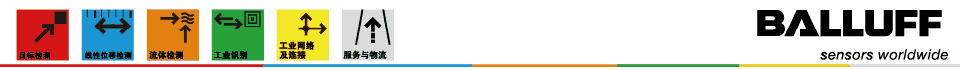再見,散戶!
于師傅算不上2011年的典型卡車用戶。更多像他這樣、靠著自己辛苦攢下的存款買上了一兩輛卡車的散戶們,最終放棄了這一讓他們感到了一些自由、快樂的營生,或無可奈何地重操舊業、返回雇傭司機隊伍之中,或干起了別的小買賣。像于師傅那樣有固定貨源和運輸線路的個體車主,已然是續留在卡車司機群體中、幸福指數最高的一小撮人了。
這只是龐大物流鏈條中微不足道的一塊碎片。
告別散戶
物流業在2011年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在百度里鍵入“物流亂象”,可以得到139萬個搜索結果。與亂收費、亂罰款等比起來,散戶們的這些事不值一提,他們如此家長里短,如此瑣碎。只是不干個體而已,并不是不能生活、生存面臨威脅。
龐大而又散亂的散戶從來都是推動中國重卡市場發展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盡管這股力量有時被直指為“擾亂物流市場秩序”的主要因素,可是它仍然執著地生存在物流生態的底端,并極具粘性地存活至今。不過現在究竟是什么讓卡車司機相繼離開了他們認為自己唯一擁有一些“技能”的行業?最終遠離了過去那種令他們既愛且恨、但卻難以割舍的辛苦生活?是什么讓他們覺得單靠自己的力量難以為繼?
2011年是個敏感的年頭:銀根緊縮,經濟疲軟,企業貸不到款,貨幣和貨物的流通急劇減少,景氣的行業很少,等等。企業運轉的停滯使物流的需求降至冰點,需求不足使運力過剩,大量司機無貨可拉、無活可干——這是許多人對散戶淡出物流業最直接的判斷。
但是,需求是否真的不足?
公路貨運似乎并不是想象中的疲軟。交通運輸部日前發布交通運輸業上半年經濟運行情況分析,上半年全國共完成公路客、貨運量分別為161億人、131億噸,分別同比增長8%、14.7%。今年前幾個月的統計數據表明,各地公路貨物運輸量較去年同期都有一定增長,并不如人們所想象, “上半年,我國客貨運輸增長較快,特別是快遞業務增幅明顯”,事實上,公路貨運需求依然旺盛。
其實對于大部分散戶來說,只要能掙到錢、能過上比另外一種生活要稍好一點點的生活,他們就不會輕易離開浸淫已久的行業。最主要的原因正如于師傅所揭示的那樣,運價始終低迷,貨源不好找,各種費稅不少交,而且隨著CPI的高企各類開支猛增,一趟活跑下來,不掙錢甚至虧錢的事比比皆是。種種生存壓力,如大山一般重重襲來,他們已無力負擔。
一個姓劉的二十歲小伙子告訴《卡車周刊》記者:“我樂意幫人開車,但我不想買車自己干,那樣太累了。”作為車主雇來的駕駛員,他和車主倒班開車,“有固定的收入,沒有經營風險,還能時不時回家看看家人,這樣的生活挺好的”。那些能堅持下來的散戶們,大多數都像于師傅那樣有著固定的貨源,指望著掙單趟的錢;或者,實在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出路。
散戶“湮滅”?
并不是有了貨運,就有散戶。作為一個群體,散戶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登上歷史舞臺。此前,卡車運輸業長期是以盤踞京津滬廣州四地的經銷商為“龍頭”,到省會及中小城市的批發商,再到小城市的批發商的三級結構。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卡車運輸業的管理權力逐漸下移至地方政府,參與者的身份增加,有國家級的國有企業、省市地方級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以及合資企業。1984年,散戶作為一個群體逐漸開始在物流業活躍起來,盡管那時候的日子并不比現在更好過——國有企業享受眾多的從業保護政策:優厚的財政補貼、燃油補貼,與運管部門盤根錯節的密切聯系,更易得到大量的高額低息貸款。不過,比起那些機構臃腫、體制僵化、服務項目有限的國有企業而言,散戶們的靈活性和快速應對能力體現了很大的競爭優勢。而且,在改革的背景下,相關部門也樂于鼓勵散戶們自立門戶為運輸業帶來有益的“補充”,畢竟這些人解決了一部分就業問題。
20世紀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散戶們迎來了自己的春天。分散在各地的個體車主,非常熟悉本地區的運輸“潛規則”,也知道去哪里找到合適的“訂單”,并能提供一些在當時看來很被需要的服務,如24小時服務、靈活的工作時間、相對更為及時的交付,等等。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卡車運輸為世代農耕的農民提供了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機會——只要你會開卡車,有駕照,還有足夠的存款購買一輛卡車,你就能當上自己的“老板”,而且掙的錢足夠讓你贏得“尊敬”。這些致命的吸引力,使這十幾年間散戶保持了每年12%左右的增速,而同期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業務沒有任何增長。
隨著中國加入WTO,物流業逐漸走向規范化運作,加之國外物流企業的進入,行業競爭進一步加劇。散戶的生存日漸艱難,他們需要自己支付過路費、燃油費、維修保養費,需要為車輛及貨物的損壞自掏腰包,需要照顧好自己,生活缺乏安全感,總是在與各種不確定的因素搏斗、掙扎,越來越多的從業者又使運價一直處在一個向下的壓力下,越來越多的散戶不得不想方設法從超載中牟利。
工況惡劣的卡車,疲勞的駕駛員,公路事故的幾率不斷攀升,最終吸引了相關主管部門的注意:超限超載車輛已經到了必須治理的程度。通過7年“治超治限”工作,盡管仍然不時有“超”標車堂而皇之地從眼前晃過,但是過去大量超載的、往返在長途運輸中的輕型、中型卡車已經鮮見蹤跡;此外,高速公路的大力建設使卡車運輸的在途時間大為縮短,2002年從成都到上海需要至少一個星期,現在全程高速下來只需要26小時——同時,過路過橋費用和油價都漲了許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基礎配套設施逐漸到位,散戶們的優勢毫無疑問將進一步退卻,他們的利潤就像海水退潮那樣迅速消失,甚至有不少人懷念從前艱苦、漫長的運輸歲月——曾使他們得到更多的回報。
本來卡車司機就是一個非常尷尬的群體,一個游走于國有企業、正規公司之外、風險與收益不成比例的群體,一個在奔波的旅程中飽食心酸、習慣隨遇而安的群體,一個面對困境不太擅長爭取自身利益的群體。他們跟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步伐,匆匆進入了當時保守而“閉塞”(此前,貨源和運輸業務為國有企業所把持)物流業,而今又隨著經濟發展的進一步深入,順應行業“規范”運作的趨勢,逐漸淡出這個或許烙印了他們父輩足跡的行業。也許有一天,終將再難尋到唱著歌兒、穿著大褲衩、點著煙、以卡車為生、熱愛卡車、粗魯又可愛的“散戶”影蹤。